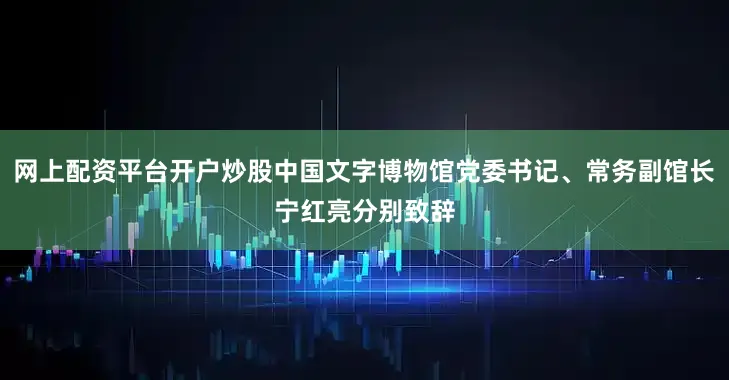毛泽东为啥选择马列主义?一文读懂
写党史时,每每看到艰难处,我就忍不住想一个问题。
如果教员他们不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,可能早就被内外各种糟心事压垮了,也只有这些由特殊材料制造的马克思主义者,才能在极端不利的环境中,在艰难的条件下,继续干革命。
进而我开始好奇,教员是从什么时候起,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呢?
教员哪怕再坚定,总不能刚出生就是马克思主义者,总得有一个过程,总得有一个契机。
这个契机是什么呢?
直到认认真真研究了青年毛泽东的一些事,才算有点脉络。
教员不是哪一瞬间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,他在这条路上走了几十年。或许从第一次看到那本列强瓜分中国的小册子后,内心就被种上了一颗种子,随后就是无数个日夜的浇灌和等待。
量变注定会引起质变,但质变需要一点机缘。机缘没有那么玄乎,不是某人说了一句话就顿悟了。
机缘是在做事的过程中积攒出来的。
全文7800字,供参考。
1
驱张运动
1919年4月,教员从北京返回湖南照顾母亲,顺带在长沙做点事。
但历史很快找上了教员。
我们说一个人的成就,固然取决于个人奋斗,但也要看天赋与历史进程。
教员还是有点历史气运在身上的。当他结束北京之行,决定先留在国内研究中国国情后,中国的历史进程,就像按下了加速键,开始飞速发展。一年一大变。
教员回到长沙不到半个月,五四运动就爆发了。
随后北京学习代表邓中夏来湖南串联,在教员帮助下,恢复了湖南学生联合会。顺理成章,教员就成为了湖南五四运动的实际领导人。
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最为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。
这个事是怎么发生的呢?
一战时,小日本见欧洲列强正在互殴,没工夫管中国,就想趁机在中国多吃多占。威逼利诱已经被皇帝梦冲昏头脑的袁世凯,签卖国的二十一条,史称五七国耻。
五七国耻被革命党人广泛宣传后,闹得很大,尤其是学生群体,受影响最深。
当时学校是宣传革命理念的重点场所,不少老师专门写了小册子介绍这个事,因此很多学生详细了解了二十一条的前因后果。爱国情绪是拉满的。教员当时还在明耻篇上写了“何以报仇,在我学子”的诗句。
1918年11月一战结束,从阵营上来讲,中国是战胜国。
按照道理,中国有权从德国这个失败国手中收回青岛等地的主权。当时中国人还很单纯,以为中国打赢了一战,就彻底翻身了,就能享受胜利国的待遇,拿回曾经失去的。
当时国人很高兴,好像从此就能告别屈辱的过去,就可以跟英美这些国家平起平坐,成为文明国家之一员了,工人、学生还有小商小贩再也不用日日忧心,大家都有美好的未来。
彼时国人,在民族危亡的压力下,忍耐了许久,太渴望胜利了,太渴望翻身了。
渴望到天真认为美国总统作为正义的代表,一定会公正对待中国这个胜利国的。甚至国内很多人,还提前开香槟,举办了“公理战胜强权”的庆典活动。
此时的国人还不晓得,尊严只在剑锋之上,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的道理。
直到巴黎和会上,英美等国拒绝了中国要求,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。
这个消息对当时国人的心理打击非常大。
尤其对国家前途抱有很多美好期望的学生群体,是非常沉重的打击。但中国青年是打不垮的,是最有朝气和力量的青年。
1919年5月1日,北大一些学生知道消息后,群情激愤,立马决定举行游行示威活动,用实际行动反抗巴黎和会的决定,打出“外争主权,内除国贼”等口号,同时确立了两条信念:
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!
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!
国亡了!同胞起来呀!
随后工商界、文化界积极响应,几乎全民参与罢课、罢工、罢市活动。
近代中国人是怎么觉醒的?
就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屈辱遭遇和失望中觉醒的。
五四运动之后,以学生为主的年轻群体,不再抱有天真的政治幻想,开始积极自救,决心效仿俄国用激烈手段改造中国社会,另起炉灶。不再把希望寄托在民主共和上了。
这一点在湖南表现的最明显。
五四运动传播到湖南后,很快就从单纯的爱国运动,转变为目标更加明确的驱张运动。
民国初期的军阀,有脑子的没几个。
但像湖南督军张敬尧这样,蠢到极致、坏出心裁的还真是独一份。
张敬尧是段祺瑞的心腹,但在反动军阀这条道路上,他比老段走得远的多,他有一个专属称号:“最反对的军阀。”
教员因他阻挠学习爱国运动要驱逐他,老蒋因他要给日本人当狗,给戴笠下令暗杀他。
张敬尧自带反动属性,深刻诠释了教员的那句名言:“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。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,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,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。”
何止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,这群人哪怕听到一丁点进步的言论,就跟有应激反应似的,浑身难受。
教员领导五四爱国游行示威活动,并不是冲着张敬尧去的,跟张敬尧也没啥关系。
但张敬尧听了教员的进步言论后,既难受,又害怕。
1919年5月7日,长沙各学校学生举行“五七”国耻纪念游行,游行队伍被张敬尧派军警强行解散,张敬尧弟弟张敬汤,还带着军警毒打抵制日货的爱国师生。
张敬尧这一手,立马让湖南学生运动找到了明确的抵制对象。
张家兄弟的父亲也挺有意思,他用尧舜禹汤作为四个儿子的名字,结果却养出一窝蛇鼠,湖南人还给张氏兄弟编了一首歌,“堂堂呼张,尧舜禹汤,一二三四,虎豹豺狼,张毒不除,湖南无望。”
张敬尧的反动嗅觉确实敏锐,很快就探到了,湖南最进步的地方在哪。
1919年8月中旬,张敬尧以宣传“过激主义”为罪名,直接出动军警包围湖南学⽣联合会,胁迫教员和彭璜等停⽌反⽇爱国运动,并且张贴布告,解散学联,查封《湘江评论》,还收缴了刚印出的《湘江评论》第五号。
反对派越是镇压,革命的力量就越是凝聚。
这是规律。
2
激烈还是温和?
张敬尧越是压迫,抵抗他的声势就越大。
湖南学生开始组建十人一组的革命团,很快就组建了400多个。湖南师生还下了决心,绝不跟张敬尧这样的货色牵扯到关系,坚决不要这样的督军和省长,“每一个湖南人都是张敬尧的敌人”。
抵抗张敬尧,随之转变为要把张敬尧驱逐出湖南。
但笔杆子只能造起声势,真正赶走张敬尧,还要靠枪杆子。
教员从来不是一个蛮干的人,他很清楚反动派不会被口号吓死,反对派还需要要更大的反动派来制。在驱张运动中,教员再次展现了他无年伦比的,利用矛盾,转化矛盾的斗争艺术。
当湖南师生第一波抗议没有取得效果时。
教员立马改变策略,开始将斗争方向改为挑动跟张敬尧有竞争关系的其他军阀。我们此前聊过护法战争,当时孙中山被湘桂军阀顶在前面,跟直皖军阀联盟形成的北京政府对抗。毛传12 | 毛泽东的第一个军事胜利,不靠枪
双方在湖南打了一仗,教员还曾智退了王汝贤的一支溃兵。后来西南军阀背刺孙中山,跟段祺瑞妥协了。
妥协的结果是湖南被瓜分,各系军阀都在湖南插了一脚。
但段祺瑞却让心腹,皖系军阀张敬尧当了湖南督军兼省长。
不管是直系军阀吴佩孚,还是湘军谭延闿,以及此前驰援湖南的王汝贤,又或者负责镇守湘西的冯玉祥等都对张敬尧有意见。凭啥这个蠢人,能当省长,吃最大的一块好处?
但张敬尧是北京政府派来的湖南省长。
只要政治格局没有变,他自己不辞职,政府也不撤他的官,军阀之间也没撕破脸,教员真拿他没办法。
驱张运动是教员进入社会后,领导的第一个重大政治运动,教员下决心要把这个事办成,要将张敬尧赶出湖南。
教员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?是激烈的呢,还是柔和的呢?
这取决于他当时的政治倾向。
教员发表在《湘江评论》上最重要的一篇文章是《民众的大联合》。此文反应了教员彼时的观念:“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哪一种,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。较大的运动,必有较大的联合”。
民众联合的基础是什么?
是由于有着反抗压迫者的“共同的利益”。
此前教员是有点偏向英雄史观的,认为个人的能力很重要,还曾在讲堂录里讲过类似,要是如今中国有一个曾国藩式的人物,何愁问题不解?的话。所以过去他认为救亡图存的关键,在于出现曾国藩这样的强人。
但通过驱张运动,实现了湖南民众的大联合,改变了教员的观念。
从此之后,教员不再只看重个人的力量,开始有意思的联合民众,依靠民众的大联合,来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。
教员当时已经看到了群众的力量,但究竟该如何使用这股力量,并没有想清楚。关于民众联合
起来后的行动方法,教员说存在着两种主张。
一种是以马克思为首的激烈派,一种是以克鲁泡特金为首的温和派。
所谓激烈就是流血的革命,所谓温和就是呼声革命。
是温和,还是激烈呢?
在《湘江评论》的创刊宣言中,教员明确表达了他的政治观点:
“主张群众联合,向强权者做持续的‘忠告运动’,实行‘呼声革命’——面包的呼声,自由的呼声,平等的呼声,——‘无血革命’。”
在驱张运动中,教员选择了温和的办法。
但教员后来提出一个著名的观点:
“矫枉必须过正,不过正不能矫枉”。
很多人根据这句话,说教员天生就是一个激烈派,天生就喜欢用破坏性最大的手段。脑子过热,把社会搞得一团糟。这是一种污蔑。
很多人不读历史,也没有做过事。
殊不知,在情绪最为激烈,在最容易上头的年纪,教员反而选择温和的手段来改造社会。此时的教员,对俄国式的激烈革命,还是持有观望态度的,担心激烈对抗会“起大扰乱”,到时死伤那么多人,不是什么好事。
而且认为强权者也是人,是我们的同类。
如果用强权打倒强权,结果得到的仍是强权。
所以在驱张运动中,教员主张使用游行示威的办法,坚持用不流血的呼吁手段来达成目的。
3
湖南自治运动
当时能管张敬尧的是北京政府。
最痛恨张敬尧的除了湖南群众,其次就是湘军谭延闿,再其次就是吴佩孚、冯玉祥这些人。
教员抓住了这些关键点,一边派人去跟湖南这些军阀交涉,鼓动他们驱张;一边成立驱张请愿团去上海、天津、北京等地,制造更大政治声势。
教员亲自率领驱张请愿团,离开⻓沙赴北京,向当局揭露张敬尧到湘后,大开烟禁,并劝⺠种烟。搜刮民财,不断增收捐税,勒索军饷等恶劣行为,先后七次组织向当局提出撤惩张敬尧的请愿。
呼声革命,说到底是要指望北京政府发一纸调令,把张敬尧免职。
但就是这样的愿望,北京政府考虑到核心利益,也不愿意撤张敬尧。道理很简单,湖南是兵家必争之地,桂系军阀、直系军阀都盯着这块肥肉,皖系军阀需要张敬尧给他们看场子。
教员们的呼声,哪有自己的切身利益重要?
所以北京政府对张敬尧的态度是死保。
但教员等人的行动,却掀起了一股反对皖系军阀的社会舆论高潮。这为直皖军阀联盟的分裂,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条件。
最后的结果是,直系军阀代表曹琨决定趁此时机,抢夺权力和地盘,跟段瑞琪翻脸。吴佩孚要带兵北上参战前,跟湘军总司令谭延闿谈好后,主动让出布防区,倒戈将军冯玉祥也给湘军的复仇让出了一条路。
1920年6月11日,谭延闿刚动身,张敬尧立马就跑了。
他弟弟张敬汤则被后来的湖南督军王占元枪决。
经过将近一年的努力,教员这群手无寸铁的学生,竟真把这件事做成了。虽然教员们很努力,但不得不承认,最后能成功驱逐张敬尧,靠的不是所谓的呼声,而是军阀内讧。
人做事,事也会反过来影响人。
驱张运动对教员的影响很大,改变了他对事情的认知。
从相信个人,到相信民众大联合是第一个改变,第二个改变是他不再相信共和方案。
教员从这场运动中,看到了中国四分五裂的事实,看到了彼时中国短期内,很难统一到一起的事实。
但教员当时只看到了表象,没有看到现象背后的本质。
直到井冈山时期,教员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立场,写了《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?》,才看到这个现象背后的本质是,中国是个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。“即地方的农业经济(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)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。”
彼时,教员看到分裂的趋势后,不再认为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共和道路,能解决中国问题,决定走联省自治道路。
“最好办法,是索性不谋总建设,索性分裂,去谋各省的分建设,实行‘各省人民自决主义’。22 行省 3 特区 2 藩地,合共 27 个地方,最好分为 27 国。”
“如此者 10 年乃至 20 年后,再有异军苍头特起,乃是彻底的总革命。”
“我曾着实想过,救湖南,救中国,图与全世界解放的⺠族携⼿,均⾮这样不⾏。”
我们在回顾 | 毛泽东为什么要走这么难的路?那篇聊过,教员选择走的路看起来很难,其实那条所有人都不愿意走的路,才是真正的捷径。教员清晰认识到这一点,所以他能坚定走下去。
但此时的教员,虽然看到了大革命这条路,但他觉得太难,没有啥希望,不如实际点先搞一省胜利。
教员首先要实行湖南的自治,要建立湖南共和国。
“那时,我强烈支持美国的‘门罗主义’和‘门户开放’政策。”
所谓门罗主义就是互不干涉。
美国在中国布局较晚,圈地较少。
但美国又不想跟列强大打出手,于是鼓吹门罗主义,要在中国搞门户开放。说白了,就是美国从实力地位出发,跟英国和日本等列强谈判,要求获得瓜分中国市场的权力。
只要给它这个权力,它就不搞事。
当时的教员还很稚嫩,没有看明白这里面的门道。
更没有看清楚,在列强瓜分中国的背景下,不可能给你搞自治的机会。列强之间没分出胜负,中国军阀混战就不会停止。湖南就一定会卷入混战中,独立只是一句空话。
教员当时只看到美国人提出的门罗主义,跟他设想中的联省自治很契合,就拿来用了。
1920年6月,教员去了一趟上海,一边筹款,一边跟陈独秀他们探讨了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。那时,陈独秀正在上海筹备组建共产党。7月教员返回长沙,开始组织湖南自治运动。
教员此时的政治观点,是比较矛盾的。
他一方面在《民众大联合》的文章里称颂十月革命,“红旗军东驰西突,扫荡了多少敌人,协约国为之改容,全世界为之震动。”但另一方面他又不赞成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来打倒强权,走的是政治改良的路子。
教员思想上的矛盾,其实是当时社会状态的反映。
五四运动后,大家都开始热烈讨论各种救国的办法,各种主义纷纷涌入的思想大潮中,其中就属社会主义思潮最为抢眼,是当时的社会热点话题,各地青年都组建了相应的刊物和社团。
但这个事热起来后,新文化运动阵营内部反而开始分裂。
李大钊和胡适先以《每周评论》为战场,爆发了著名的主义和问题之争。这个争论的导火索是皖系政治首领、时任北洋政府众议院议长的王揖唐,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蹭流量,谈论社会主义。
他认为,中国古已有“均田均耕”等与“近世之共产主义相近”的学说,但自古也有人认为这种学说“与中国不适”。大意是,这些东西吵来吵去没有用,不如研究研究如何让老百姓过得好一点。
胡适看了之后,深有感触,于是主张“多研究些问题,少谈些‘主义’”。
第一个反对胡适观点的是蓝公武,他说:“主义好像航海的罗盘针,或是灯台上的照海灯”,批评胡适的观点是因果倒置。尤其最后的总结,讲的很好:我们要解决种种问题就要研究种种主义,所以,“主义的研究和鼓吹,是解决问题的最重要的切实的第一步”。
第二个反对胡适观点的是李大钊。
李大钊给胡适写了一封信,认为“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”,为此“惟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”“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”。
随后就引爆了主义和问题之争。
没有对主义的坚持,就没有筹备共产党的动作。有了坚定的主义,才有创建党的需要,有了党,革命才有了核心,才有后来的抗日核心,新中国的核心。
要是按照胡适的路走,中国最好的结局就是成为美国附庸,独立自主的新中国是不可能诞生的。
这个争论对我启发很大,我以前并不注意对“道”的理解,一门心思的研究掌握“术”。
后来才明白,主义和问题之间的关系,就是本质和现象之间的关系,道是术的根本,术是道的体现。
问题就如过江之鲫,不抓住根本问题,是解决不完的,掌握再多术都没有用。
教员当时其实比较倾向胡适,响应胡适的观点写了很多需要研究的问题,还准备成立一个问题研究会。后来不了了之了。
不仅李大钊和胡适分裂,新民学社内部也开始分裂。
远在法国的萧子升和蔡和森也因为革命道路问题,发生了激烈争论,蔡和森认为只有采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,才能改造中国社会。萧子升则坚持温和的革命,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。
谁也无法说服谁,于是写信给教员,让他做裁判。
但那时教员自己都没有想清楚,究竟哪条路才是正确的,哪条路是错误的。
答案不是想出来的,而是做出来的。
在组织湖南自治运动的过程,教员找到了答案。
4
矫枉必须过正
湖南民众自治是教员这一时期较为系统的政治观点。
但老练的军阀谭延闿,立马就把教员好不容易鼓吹出来的舆论声势,当成了个人集权的工具。
他以地方自治为名,企图包办“制宪”,召集官绅名流和省议员开“⾃治会议”,提出“湖南自治法”,省议会即以“民意机关”自居,并组织“自治研究会”。要把民众排除在外。
没有枪杆子作为依仗的革命群众,没有革命理论作为指导的群众运动,最后的结局就是沦为野心家的夺权工具。
群众情感越激烈,工具就越趁手。
尽管教员很快就发现了猫腻,但还是不可避免沦为军阀内斗的工具。
当教员等人反对谭延闿的制宪方法时,另一个政治骗子登场了。
“一个名叫赵恒惕的军阀利用‘湖南独立’运动来谋取私利,把谭延闿从湖南赶了出去。他装作支持这场运动,拥护中国联省自治的主张。然而,他一当权就开始大力镇压民主运动。”
赵恒惕挤走谭延闿,继任湘军总司令,打一开始就是为了夺权。
权力一到手,再无顾忌,立马用暴力压制所有民主的要求。
当时有一幕场景,哪怕几十年后,教员也记得清清楚楚,当时新民学会为庆祝俄国十月革命三周年,上街游行,却被警察镇压了,教员等示威者跟警察据理力争,根据宪法多少多少条,民众有集会、结社等等权力。
警察是怎么回答的?
“他们答道,他们到这里来不是为了听宪法课,而是要执行省长赵恒惕的命令。”
轰轰烈烈的湖南自治运动,就此宣布失败。
革命虽然没有成功,但教员却受到了教育。
谭延闿和赵恒惕两位湖南军阀,让年轻的毛泽东认识到:
只有通过群众行动夺取政权,才能确保实现有力的改革。他不再相信什么呼声革命,开始认识到革命不是请客吃饭,不是做文章,不是绘画绣花。革命是暴动。
1920年11月中旬,教员给许多友人写了信,既是总结失败经验,也是对自己这一阶段思想的反思总结。
在给向警予中的信中,教员写到:
"教育未行,民智未启,多数之湘人,犹在睡梦...湖南人脑筋不清晰,无理想,无远计,几个月来,已看透了。政治界暮气已深,腐败已甚,政治改良一途,可谓绝无希望。”
教员的政治观念大变,思想中再无幻想的那一面,开始变得坚定起来,逐渐接纳了列宁为代表的激烈派。
并对胡适“少谈些主义”的观点,有了不一样的看法。
11月25日,在给罗章龙的信中,教员说到:
“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所共同信守的‘主义’,没有主义,是造不成空气的...主义譬如一面旗子,旗子立起来了,大家才有所指望,才知所趋赴。”
兜兜转转,教员最终还是坚定选择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理。接受了只有采取激烈的手段,夺取政权实行专政,才能保卫革命果实的事实。
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,相信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,之后就再也没有动摇过。
后来跟斯诺回忆往事时,教员还清晰记得,
“1920年冬天,我头一回在政治上将工人们组织起来。在这一过程中,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开始对我起指引的作用。”
“我从此也自认为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。”
教员从来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,他的思想有一个变化的过程,他也曾对军阀有过幻想,对政治改良抱有希望。但事实教育了他,也改变了他。
人做事是为了改变结果,然而,事也会反过来改变人。
因为人在做事的过程中,会遇到问题,遇到人和事,这些东西就像子弹,把你自认为是铜墙铁壁,正确的旧认知,打得稀巴烂,打到你不得不否定自己,直到尝试改变点什么为结束。
当你从头到尾做完了一件事,不管最后是成功还是失败。
它都会成为你的一部分,成为你身体中最有分量的那一部分。
完。
顺阳网配资-正规的股票场外配资平台-线上最大的配资平台-低息配资公司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